石計生教授最新研究文章:正聲電台與台灣歌謠:雲林播送頭周蓬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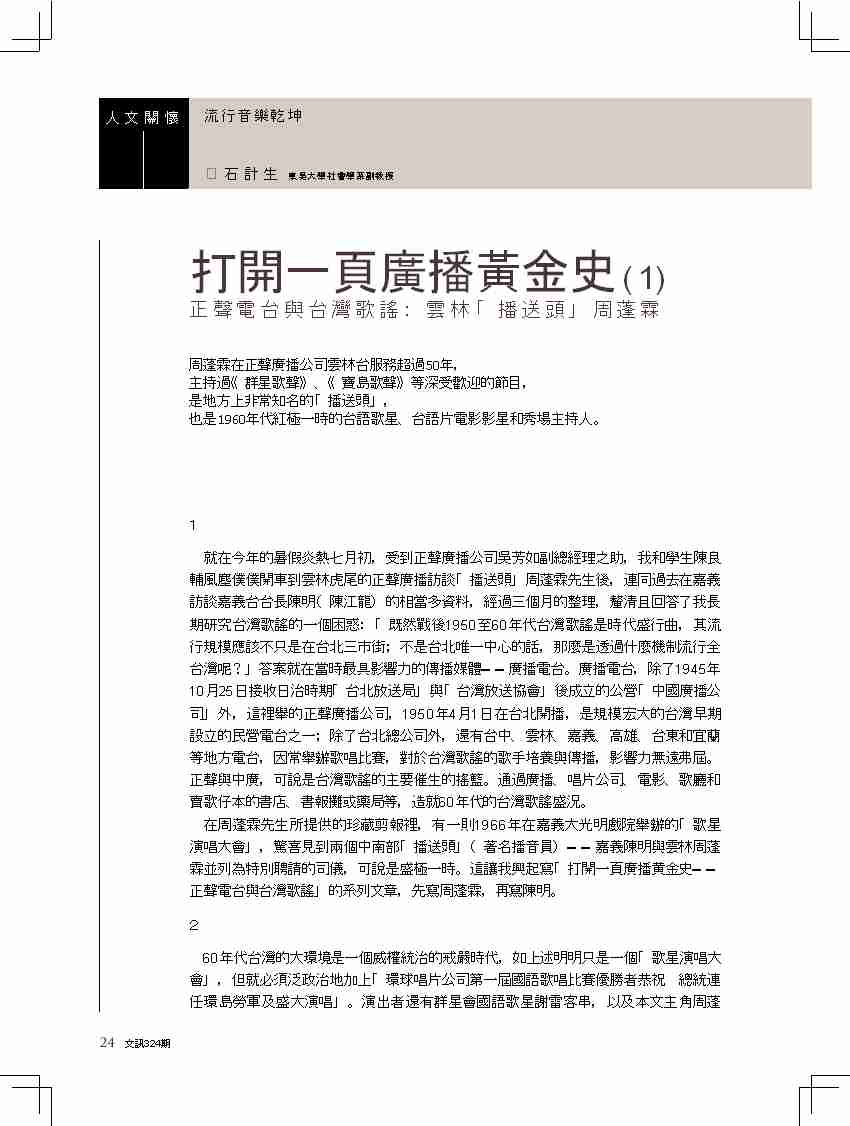
打開一頁廣播黃金史(1)
正聲電台與台灣歌謠:雲林「播送頭」周蓬霖
◆
1
就在今年的暑假炎熱七月初,受到正聲廣播公司吳芳如副總經理之助,我和學生陳良輔風塵僕僕開車到雲林虎尾的正聲廣播訪談「播送頭」周蓬霖先生後,連同過去在嘉義訪談嘉義台台長陳明(陳江龍)的相當多資料,經過三個月的整理,釐清且回答了我長期研究台灣歌謠的一個困惑:「既然戰後1950至60年代台灣歌謠是時代盛行曲,其流行規模應該不只是在台北三市街;不是台北唯一中心的話,那麼是透過什麼機制流行全台灣呢?」答案就在當時最具影響力的傳播媒體——廣播電台。廣播電台,除了
在周蓬霖先生所提供的珍藏剪報裡,有一則1966年在嘉義大光明戲院舉辦的「歌星演唱大會」,驚喜見到兩個中南部「播送頭」(著名播音員)——嘉義陳明與雲林周蓬霖並列為特別聘請的司儀,可說是盛極一時。這讓我興起寫「打開一頁廣播黃金史——正聲電台與台灣歌謠」的系列文章,先寫周蓬霖,再寫陳明。
2
60年代台灣的大環境是一個威權統治的戒嚴時代,如上述明明只是一個「歌星演唱大會」,但就必須泛政治地加上「環球唱片公司第一屆國語歌唱比賽優勝者恭祝 總統連任環島勞軍及盛大演唱」。演出者還有群星會國語歌星謝雷客串,以及本文主角周蓬霖。這也足以說明,在電視風行前,「播送頭」是跨足國台語的歌唱世界,舉足輕重。
周蓬霖於1965年考進正聲雲林台,他在正聲廣播公司雲林台服務超過50年,主持過《群星歌聲》、《寶島歌聲》等深受歡迎的節目,是地方上非常知名的「播送頭」,也是當時紅極一時的台語歌星、台語片電影影星和秀場主持人。周蓬霖的發跡與他和邱蘭芬(當時只有九歲,後來以演唱電視布袋戲〈苦海女神龍〉一曲紅遍全台)合唱的一首由葉俊麟作詞、林禮涵作曲的〈春宵舞伴〉台灣歌謠有關;
但為什麼在我們研究的台灣歌謠一線歌星裡,從來沒有「周蓬霖」三個字?我在雲林訪談時,心裡一直思考著。第一個原因可能與台北中心視角創造的城鄉差距有關:在台北之外就是邊緣,或者不存在,這是到現在仍是如此的新聞的、媒體的、歌謠的甚至生活的傲慢「天龍國」問題。雲林虎尾是三級城市,就被徹底地方化。如上述兩則訊息,都是來自當時大台中區第一大報《台灣日報》,影響力只在中南部,北部很難得知。但這並不意味著台北的流行可以沒有中南部而獨大,台灣的西部走廊不但是經濟命脈之所繫,其由市場機能導引的縱貫線,更是流行音樂靈魂環環相扣的演出與傳遞歌謠的空間連續體,其實中部本身就有一個豐富流行展演網絡。1965年的「獅王唱片公司歌唱發表大會」傳單和剪報就透露了這樣一個60年代大台中區域綿密流行空間,甚至在今日鮮少被注目的幾個中部城鎮:雲林虎尾(黃金戲院)、斗六(遠東戲院)、斗南(斗南戲院),南投(南投戲院)、水裡(美都麗戲院)、埔里(能高戲院),台中豐原、清水等地的戲院,有著緊密的連續演出(而且我很懷疑這些戲院在日治時期極可能就存在,以XX座原名,戰後被改成XX戲院繼續使用。如台北大稻埕的演出混合館永樂座戰後被改成永樂戲院)。值得注意的是:正聲廣播公司第八次台語流行歌曲比賽亞軍陳永龍被重金禮聘參加;而本身是正聲播送頭的周蓬霖,也被冠以「中音紅歌星」參與演出。名單裡最令人熟悉的是在台北歌壇以〈落大雨的彼一日〉聲名大噪的鄭日清也被邀請至中部。台語片電影諧星邱罔舍、康丁都在列。
1967年由正聲廣播台中農民廣播電台和大康製藥公司合辦的「歌星選拔大會」,在台中的「新舞台戲院」演出。傳單左下角可見門票代售處有唱片行、西藥行和眼鏡行,都位於台中的戲院旁或市場邊,形成有趣的台灣歌謠流傳共同體。最下面的「人人保密,人人防諜」說明了這仍然是戒嚴時期的娛樂事業,只是隨著台灣歌謠的盛極流行,恐怕大家都心知肚明,那些政治性箝制與標語,最終都進不了人民的心裡,最後都流於形式,人民的耳朵通過自己的感覺成為理論家。除了周蓬霖外,邀請到的是台灣歌謠、台語片電影甚至國語歌壇等全國知名的一線紅星:吳晉淮、葉啟田、黃西田、良山、劉福助、郭大誠、邱蘭芬(當時還是小妹妹)、白櫻、尤君和美黛等,眾星雲集,顯示了台中市作為台灣中部最大城市的非凡氣度與排場。演出是一天四場,全票十五元,半票十元。據周蓬霖說,是盛況空前,場場爆滿!大家愛聽歌,台北也要來到台中演出。這直接說明了一個事實:大台中區域的台灣歌謠市場極為龐大,也有設備完善的聆聽場地與網絡,不僅是台中市,就連周邊的豐原、清水、虎尾、斗六、斗南、南投、水裡、埔里等二三級城鎮/農村,都有綿綿不絕的台灣歌謠與共生的台語片電影演出。其中最重要的樞紐就是電台,正聲廣播公司的電台網絡,促使這一切成為可能。從今日來看,電視時代所瓦解的,不但是完全靠實力的「沒有臉龐的歌手」(singer without face)的崩解,變成搔首弄姿,依靠外表的虛度;更可怕的是資源集中於北部,瓦解掉台北以外原本活活潑潑的台灣歌謠與人民日常生活的聆聽世界,特別是上述的二三級城鎮/農村流行網絡,進一步撕裂城鄉與南、中、北差距。
而第二個理由可能是因為周蓬霖沒被選入當時設備最好,規模最大的由蔡文華創立的台南亞洲唱片行的台灣歌謠歌手典藏集。這當然令人很好奇。〈春宵舞伴〉既然如此受歡迎,亞洲唱片沒有理由不找他灌錄唱片,或許是因為某些地緣因素,或者周蓬霖已經先在邱蘭芬父親邱清泉創立的「聲寶唱片」出唱片並簽約的結果。即使如此,周蓬霖的根本身分「播音員」,仍然通過正聲廣播的全台覆蓋系統,甚至跨越至海峽對岸的穿透力,讓他成為一個奇特的台灣歌謠傳播公路裡的中部樞紐,正聲雲林虎尾台幾乎天天訪客不斷。
1960年電視伊始、沒有高速公路的省道時代,周蓬霖是當時全國十大播音員之一,具有很大的影響力。當時的台灣歌謠巨星文夏、洪一峰等北高來往演唱時,都會從台中轉至雲林虎尾找周蓬霖,上節目打歌與敘舊。1967年10月份《廣播雜誌》署名張蕙(另一虎尾台廣播員)就寫道:「金馬影業公司董事長蘇南竹先生、影歌星洪一峰先生、麗娜、莎莉小姐,日前來電台訪問,周小生主持的『寶島歌聲』節目裡穿插錄音訪問與現場唱歌,因對話幽默甚得聽眾好感,所以引得大批迷哥迷姊湧向電台爭睹大明星廬山真面目」。「周小生」就是周蓬霖。周蓬霖也與寶島歌后紀露霞熟識,暱稱之為「紀阿姨」。我問他文夏、洪一峰和紀露霞的「二王一后」稱號是否60年代就有?周蓬霖說確實。那是由當時的台灣播音員共同選出而公認的「二王一后」,地位無可比擬。
3
當我們打開一頁廣播黃金史,去看正聲電台與台灣歌謠的關係時,經由研究訪談發現了雲林「播送頭」周蓬霖,這被忽略的多才多藝的重要人物。周蓬霖不只是主持廣播,也出唱片,用筆名「一西」寫台灣歌謠歌詞、演台語片電影。我在雲林虎尾台現場看到的唱片至少有七張黑膠,其中幾張十吋唱片有和邱蘭芬11歲時一起出的唱片,更令人驚喜的有洪一峰唱的幾首從未聽過的曲目。周蓬霖演的電影包括:《流浪到台北》(與黃西田)、《歌星淚》(與洪一峰)、《港都夜雨》(與西卿)和《聖旨》(與江明),雖然配角居多,仍可以說紅極一時。我問周蓬霖拍片都在哪裡?他說都有,「像《歌星淚》就在台南拍,而且拍得很快,幾個星期就拍完了。通常是導演拿劇本給我看,背熟了就去拍。」
我對於60年代唱片如何銷售的問題很感興趣。周蓬霖說,「像和邱蘭芬一起出的聲寶唱片,就是邱蘭芬的爸爸邱清泉組織的唱片製片場與公司。」通常就是運到台中的好萊塢唱片行,這是大盤商(有點像台北西門町中華商場的哥倫比亞唱片行等),再運銷至中盤、小盤至全台各地唱片行據點。通過廣播,與歌廳和唱片行連結,農村包圍台北中心城市,農村逃逸線建構流行,這就是大台中區域的台灣歌謠真實之一面。周蓬霖做為播音員,在那個年代有點像現在電視綜藝節目天王張菲的地位,深受聽眾歡迎。他說虎尾、台南、台中等地大歌廳開幕,都會找他去登台主持造勢,花籃常常擺到沒有地方放,可見受歡迎之程度。在那個戒嚴又禁歌的時代,國民政府不讓大家唱台語歌,主要是在電視節目與廣播的審查。「表面上配合政策是為了混口飯吃」,周蓬霖說,「但聽眾就是喜歡唱台灣歌謠、聽台語歌嘛,所以唱片暢銷和歌廳天天爆滿,就證明了台灣歌謠的韌性與活力吧!」我設想的台灣歌謠研究新的理論性概念「地下迴路」(underground circuit)確實就被證實也浮現其意義端倪。
訪談後我們與正聲廣播雲林虎尾台現任台長蔡梓禎一起去參觀正聲雲林虎尾台的原址,非常60年代樸素的建築風格,裡面有周蓬霖為台灣歌謠奉獻一生的回憶,道別時在夕陽中深深令人感動。
(2012.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