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 彩虹
養諸有情有如地
如此等待彩虹降臨那時光
秋之天問(為我的吳忠吉老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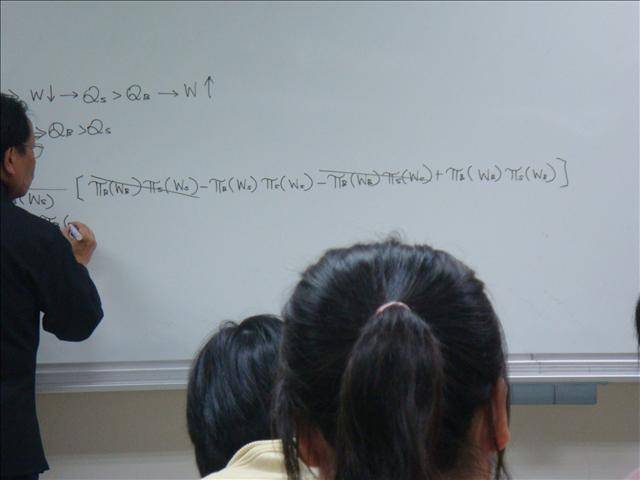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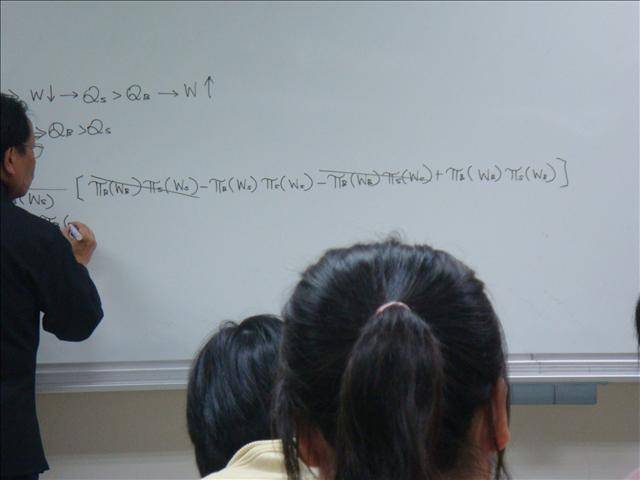
經過了整個台北城瘋狂赭紅到令人不安的台灣巒樹,我趕到台大醫院加護病房已經是下午兩點一刻了,老師,第一眼看見您的時候那淚水終究是被我忍住了。穿上了隔離衣,戴上口罩,那深冷白冰的不鏽鋼門緩緩打開,4B2,一個憔悴的婦人坐在病榻旁,是師母。引我坐在您的插滿管子的身旁。說了一些您自七月在師大上課不小心跌倒送醫院以來的種種,本來要出院了,卻因為醫院的誤診而導致病情加重,終至昏迷腦死。「為什麼?」「這是什麼醫院什麼世界?」「是誰奪走我的恩師?」我的心裡憤怒地問。師母以一種非常平和的語氣說著七月以來老師在醫院裡的起伏。我假裝靜靜地聽著。看著人工呼吸機器供應著老師的一分鐘8次的呼吸的次數。看著老師微開無法轉動的眼睛。前塵往事歷歷在前。「老師還是聽得到你說話,我出去,你是老師的得意門生,你跟老師好好說說話,但不要哭」,師母說著就走出病房。我坐下來。想握著老師的手,但觸不著。我只好搭著老師的肩,跟老師說話。
老師,學生來晚了。整整遲了三個月。非常的自責。若不是昨天到台大去講課,我還不知道。老師。您是我的恩師。照顧我最多。啟蒙我最多。教誨我最多。在我的那青春瘋狂的台大青年時代。特別是1985年的那年5月,我們佔領了傅鐘,並且發動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學潮。國民黨的軍警把台大外圍團團圍住,便衣刑警到處都是。老師,您記得嗎?在那時候,有一天你忽然把我找到傅鐘旁的行政大樓您當註冊組長時的辦公室去,拿出一份名單,說「警備總部已經知會孫震校長,學生運動已經危及社會國家安全,這23人名單中有計生你,你要小心。但老師會全力保護你們的,我會跟校長說,學生們爭取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是純潔的,沒有任何其他目的的。」老師,我們沒有一個人在那次運動中被逮捕,不用說就是您的說項奏效了。若沒有您,老師,我想我的一生是完全地不同,可能在綠島步上政治犯的後塵,也可能曝屍荒野。老師,謝謝您!你給我的是一份對於土地不悔的愛, 一種為理想奮不顧身去追尋知識的無上勇氣與毅力,一個從擦鞋童變成台大經濟系教授的無產階級找到自己的典範。老師,我把昨天寫在部落格的心情現在再說一遍給您聽:
「就是昨日下午至台大普通教室504講授「文學中的台大」課程,於中間休息時一經濟系學生問問題,閒聊之際,驚聞我的恩師吳忠吉教授重病住院,第二節課上來精神分離,力掩心中擔憂不定,午夜輾轉反側猶不得眠。我那時是唸經濟系的大三時代終於敢和導師老師深談就是在當時只有兩層樓的普通教室。我在一樓的教室外等吳老師下課,看他在黑板寫著高深莫測的數學公式會心一笑,知道那只是戒嚴時期的偽裝。老師出來後就跟我一起步行走向新生南路,「計生,你那厚重的包包裡裝的是什麼?」「一些馬克思理論,和社會主義的東西」,老師咧嘴用台語笑著拍拍我肩膀說「金好,金好」,我跟著笑,感覺在一個人人想去美國留學或進銀行上班的沒人理解我為什麼搞學生運動抵抗戒嚴體制的時代有個暗夜明燈的溫暖,一路跟老師一起到懷恩堂那頭的咖啡廳繼續討論。吳老師最為驚人的能力,是能夠用主流經濟學的P&Q圖式直接畫出資本家是如何剝削勞工而非法佔有剩餘價值(即超額利潤),我記得當年在那昏黃咖啡廳下聽得目瞪口呆!原來主流經濟學與馬克思理論並非我想像中的遙遠,這啟迪了後來我在《馬克思學–經濟先行的社會典範論》書中的打通馬克思與凱因斯經濟理論的艱鉅工作。憶起吾師在我的戒嚴時期的大學時代,於政治經濟學的教誨、口傳心授堅決理想的意志和呵護有加的生活關懷,使我這到處尋找回家的感覺的漂泊心靈不禁潸然淚下。噫!悾傯世事,國事飄搖,而師恩此生難報,繼起者可不孜矻於大愛傳播與追求永恆之事業者乎。」老師,您一定記得普通教室前的我們的對話吧
老師,我很想念您,很愛您。今年中秋寄柚子到您家沒有接到您的電話當時就覺得有點奇怪,後來瞎忙就沒問您,沒想到就出事了。老師,學生來晚了。整整遲了三個月。非常的自責。若是三個月前,我想以我的氣功能耐一定可以幫老師復原。現在。老師,我只能對您看來像是自言自語地說給您聽。我哽咽了幾次。無法言語。我繼續說,心中充滿悲傷,但我不流淚。師母說。不流淚。
師母進來了。帶著一種秋盡冬將至的蒼涼,宛若巒樹的燦爛黃花晦暗成赭紅的憂鬱,口罩上方疲憊的眼神看著我,示意要我洗了手到外面繼續說。老師。您不用聽也知道。以您的過人智慧與毅力知道時之將至,可以放手去天國。老師,是作學生的不捨。您才63歲。學生要跟您學習的東西還很多。您跟我說「不要當第一個站起來的人,要當最後一個倒下的人」為什麼現在您要棄學生而去,讓我孤單一人面對這險惡世界?老師,我問秋天的蒼天,它只給我濛濛細雨的回答。不是一個回答,而是敷衍。所以。老師,我要您醒過來,您一定要醒過來,我要為您求遍天下神祇,或者無神論的堅強意志也可以。你前半生的台北街頭吃苦的意志,在我大學時代就已經完全感染了我,現在,老師,學生要求您感染您自己,從死神掌中脫離,回到這多麼需要您經濟學智慧的台灣!回到只學到您一身功夫萬分之一的學生旁,再親自接受您的教誨。老師,剛才我還對您說了這些話,您聽見了嗎?
秋之台北城,一樣忙碌,我從台大醫院趕回外雙谿研究室準備開會前寫了這些。學生打電話來催。我說等等。這些冗長假民主的鬼會都必須等等。我必須寫完這些。我必須對秋天的宇宙發問,而灰白相間走得極快的浮雲,預示著風雨或許將至,我的胸臆焚燒著即將喪親之痛的篝火,把眼前的校園裡的台灣巒樹燒的更為火紅,更為悲涼,更為思念我的老師吳忠吉。而背手轉身出了308研究室右轉扶著陳舊鐵欄杆抬頭所見,濛濛細雨裡,一道意料之中的彩虹意料之外在我的淚痕中出現,從故宮的方向彎向市中心的台大醫院,老師,加護病房4B2,您在那裡沈著呼吸著,也看見了這聯繫我們師生情誼的七種色彩交織而成的無窮無盡變化的彩虹嗎?您必然也看到了吧,已經五點多了,天逐漸黯淡下來了,老師,您好好睡,明早醒來,學生再說些以前我們有趣的掌故給您聽。老師,您好好睡,彩虹裡安眠,祝您有個美麗燦爛的夢,我在黎明來臨時等您,一起公館溫羅汀散個步,說說天下大事,人生哲理,與這個屬於秋天應該有的期盼過了冬天,春天就會不遠,彩虹會消散,老師,我對您的愛永不止息
(2008.10.16)

老師,在我們渡過的那個只知道解除魔咒卻不知留下記錄的時代,學生突然發覺經過了二十多年的相處,無數次見面、聚餐與討論學問,我竟然連一張和老師您的合照都沒有,我只能放上昨天下午瞥見的彩虹成為一座橋,聯繫這頭與那頭。我昨天看著您無法回首動彈的臉,假裝沒事地走了,和師母道別,和您的大女兒還在台大經濟所唸博士班的女兒道別,回來山林懷抱中的外雙谿,我寫下了「秋之天問」,我假裝沒事開會,讓書僮離開讓生活自己,我努力讓自己安靜。我確實安靜了。然後另一個白天來臨,我打開電腦。老師,我發覺這世上還是有很多人關心您。您以前的學生。豆腐魚。以及其他人。寫e-mail信來。說「我們都很關心吳忠吉老師」。還說要去4B2看您。給您力量。老師。我現在坐在308研究室。聽著學生捎來的陳昇「把悲傷留給自己」。我已經很久不曾如此濫情到任意淚流滿面。在獨自一人的空間中,我想是合理的,被允許的。老師,我看著窗外的一樣的老榕樹。與後面的女生宿舍。一些不會再回來的人影。我往後看。更高的雞南山後。不會再回來的爬坡撐傘旅行。我再往後看。不會再回來的台北盆地的南方。在法學院。在溫羅汀。您以威嚴清晰的論證,單刀直入地說明資本主義經濟的真相。站在勞工這一方的發言。記得當時要出國留學時,您還要我去讀倫敦政經學院,說那裡是馬克思的第二故鄉,勞工研究非常的好。回來可以貢獻所長。為台灣。後來我去了芝加哥。回來應徵教職。有幾個可能。當我懸而未決時,我心裡想到的第一個問的人就是老師您。後來又有機會轉到別的學校去。我也是問您的意見。老師。事實證明。您給我的意見都是對的。更早之前,甚至,我所認識的女孩,也要讓您與師母看過才是安心的,雖然我這個人漂泊無定性十足浪子如您所說的有你年輕時的影子。老師,您記得那時師母為了你健康家裡禁煙那次您假借送我下樓從你家中偷溜下來一起抽煙時您笑著跟我說的話嗎?「雖然天性流浪,但每次的愛都要專注泊港,直到緣聚緣散,一如清風吹白雲」,4B2中沈著呼吸的您,老師您記得嗎?
但老師,我們這麼親近,從那解除戒嚴魔咒的時代迄今,為何我們竟然沒有一張合照呢?是不是因為我一直覺得您作為我生命中的明燈,會永遠在那裡呢?還是您刻意留白讓我必須一輩子用文字記住您的影像呢?我在研究室俯首,書寫,抬頭,你的影像無處不在。略呈倒三角形的頭顱,顯示巨大腦容量蘊含龐大的思維能力,兩顆炯炯有神的眼睛威嚴沈著地看著我,令不認識您的任何人不寒而慄。但是,當您一開口,或者聽到您的綿密推論、笑聲與台語時,我整個向來戒備不信任人精神分裂的心就如融化的冰雪,與您愉悅交融,如沐春風。老師,我在東吳上課時。少數親近的學生曾經用這樣的眼神與距離形容我。那冰雪融化的感覺也是一樣的。老師。我想我正繼承起您的傳道授業解惑的衣缽吧。老師,書寫了這一嚮午。我的剛才的眼淚也隨著太陽雨的狐狸嫁完女兒的停歇光影輕灑在老榕樹紛吐的褐色氣根上閃爍風中飄逸風乾了。老師,我和眾多您教過的台大的,師大的或者其他學校親炙或私淑的學生們一起祈禱著奇蹟出現。您一定要醒過來。跟我好好照張相。老師,我會說服師母的,可以的,一起抽跟煙,照張相。不然我也會拿起狐狸給我的那把小刀披荊斬棘,到那千萬種顏色的廣漠山谷盡頭所見的碩大無比的彩虹前,去找尋老師您的靈魂所要去的地方,那吳忠吉經濟學所構成獨一無二的美學,不分階級的真善美的究竟之地,老師,那影像,那域土,我以一生的心力去追尋
(2008.1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