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志之愛
我的同志之愛 /石計生
這天下午我忙碌主任公務差不多時,兩個大學部來到我向來敞開的辦公室,一個劈頭就問我,關於婚姻平權法案的看法。過程中,生長於基督教喀爾文派家庭的這學生,也清楚說明了自己反對的立場和邏輯,但仍想請教老師的意見。台灣是真的自由民主,老師欣賞你的表達看法,但
我堅決支持婚姻平權法案,其中有生命經驗的理由,也有思想高度的理由。
我沈吟,看著他端坐的方向,指著窗明几淨上的相框的海報。說老師留學美國時的好朋友比爾華格納 Prof. Bill Wagner 就是同性戀,而且今年剛結婚,對象是來自上海的好青年,在同性婚姻合法的加州,受到眾人祝福,幸福快樂過日子。我說,如果不是比爾,我在美利堅共和國大概畢不了業。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時光因為我的同性之愛而獲得拯救。
我剛到美國的第一年適應不良,精神瀕臨崩潰,又強烈感受到白人對我們華人的種族歧視,只有比爾用深刻的友誼讓我在異邦感受到溫暖。在一起討論高等統計學和到downtown 小酌的過程中,我們成為莫逆之交,也讓我在台灣傳統家庭教育下的異性戀中心觀點產生了決定性的轉變。春夏秋冬遞嬗,記憶裡的隆冬散步,和他當時的男友Vick, 另外同學Terrance Steward, Jim Gramlich 等共渡芝加哥的起伏。因為愛的四年,我順利完成學業歸國教書。
我的同志之愛可以說是比愛情更為深刻的友誼。而且,是生命經驗讓我的同志之愛進入我的學術思維。
社會學理論課,下學期我們會上到褔柯(M. Foucault), 我對學生説。關於同性婚姻平等法通過後,你所擔心的爺孫畸戀或家庭倫理崩解造成社會秩序大亂。我說,這並非是同性或異性戀的問題,而是作為人的品質的問題。如我的同性之愛,比爾教授,是我所遇過最溫暖、最好的人。我們這裡談的是作為一個人的基本權利和價值,而且這個價值不應該是以異性戀為中心的法律去鞏固社會偏見。難道同性戀的台大畢安生教授自殺悲劇的社會啓迪還不夠嗎?
我說。沒有人在恢復同志之愛上比褔柯説得更透澈。愛及其伴隨的欲望,不分同或異性,是一種風格而不是道德、宗教的或法律的問題。
褔柯三大卷的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所有反對同性婚姻的人都應該認真閲讀。古希臘為何是人類社會的一個典範?至少在面對性欲上是尊重各種欲望風格的。不是同性或異性戀造成社會問題,而是你能不能自律(self-discipline)、產生和天地自然配合的欲望風格的問題。這褔柯稱為aphrodisia,古希臘人在desire 欲望與logos理性 間追求動態平衡的過程,這個高度
就是這個高度,我說,讓我們脫離了可耻的對同性戀的汚蔑和歧視,回復同志本來就有的自由和平等。同性戀有千年歷史,他的被貶低、歧視,根據《性史》,是中世紀黑暗時代的教權獨大後至今日的資本主義社會逐漸形成,一個為了不斷強化生產力累積資本,強迫性重覆地大禁閉懲罰不事生產者如同性戀、乞丐或詩人等,建構以異性戀中心的一夫一妻制的世界觀,用法律定同性之罪。古希臘的自律降格為資本主義的他律。
明日的同性婚姻平權法案,我認為只是恢復人類的基本權利和價值,揚棄掉因為歷史偏見而造成同性之愛的悲劇和苦難。我們台灣做為民主社會的國家,有能力而且可以向亞洲和全世界證明,通過同性婚姻平等法不僅不會天下大亂,而且會讓我們邁向更好的未來。
學生說,老師,我眀天還是會去遊行。我說,非常好。最優秀的學生不是只會作筆記的學生,而是在實踐中思考和改變觀念的學生。我說今晚和我一起讀羅馬書15章14節:「弟兄們,我自己也深信你們是滿有良善,充足了諸般的知識,也能彼此勸戒。」And I myself also am persuaded of you, my brethren, that ye also are full of goodness, filled with all knowledge, able also to admonish one another. 我親愛的學生,我以主耶穌之名祝福你,阿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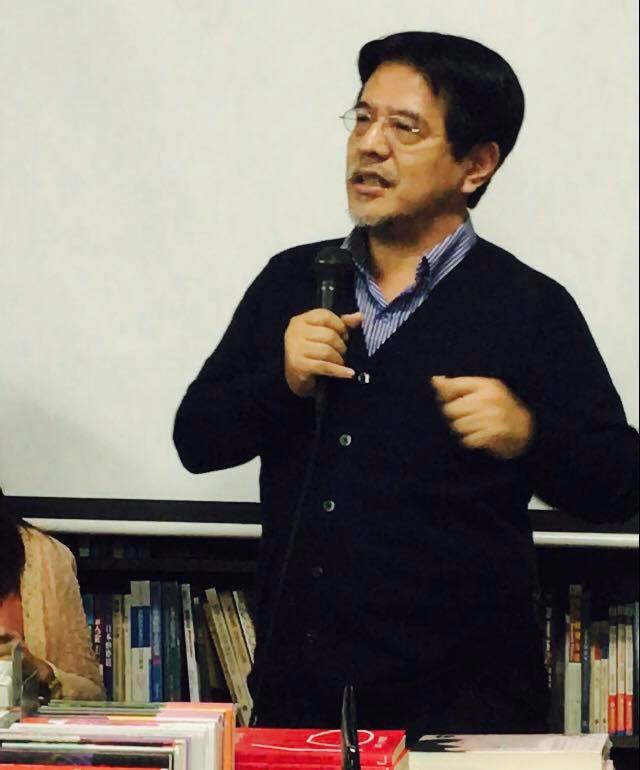



 別有憂愁,為愛守候(都市更新受害戶士林王家筆記
別有憂愁,為愛守候(都市更新受害戶士林王家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