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記
七日記
「 在那些日子裡,人要求死,絕不得死;願意死,死卻遠避他們。」 — 啟示錄(Revelation) 9:6
「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啟示錄(Revelation) 21:4
◎ 石計生
【第一日】
習慣地我選擇木柵線動物園站的最前面的車廂的進門左轉靠窗的第一個位置,進入褥夏的當口,因為這裡可以放置那沈重的背包與夫眺望捷運沿線的山水與臉龐日日再出發。你這次以一老者的形象出現,頭戴著花格子的灰帽,一臉未整理的稀疏鬍鬚,帶著一付黑框老式眼鏡,蹣跚地由後方上車,從木柵站。我其實是認識你的,不然的話為何我會警覺你濃厚凝重的呼吸聲裡夾雜著嚴肅的咳嗽聲訴說著你習於獵取人們的靈魂的化身,就這麼坐下來,就坐在我的左側。車行迅速穿越麟光站後的詭譎山洞,長長黑暗的山洞10秒瞬間而過,你,我可以以眼角餘光瞥見你,陰暗皺紋滿布的眉宇透過黯淡的節奏依然的咳嗽向我傳來一個訊息,就像你向所天下人宣示的訊息,像汪洋中絕望的號角,吹奏著過往風帆的輓歌:
我的陰影,將降臨於你的身上
這訊息淡淡的、如茉莉花開放在六月的枝頭
或將是美麗而明確的萎索?
【第二日】
你在什麼站下車說實話我渾然遺忘,回國以來捷運裡人來人往我不曾記憶著些什麼,你是我唯一有印象的人,在失速的過往與未來支離破碎的你我。上次你以和尚的形象帶走我摯愛的父親時我沒有哭我只是十分想念他,他的背影在熊熊火光中煙消雲散,只剩下夢裡似真非假的問候與家居。心愛的人死了,到處是地獄。你這次清楚認真的也想帶走我,就像你七年前帶走我父親一樣。我說,但此時我並不能像20歲時那樣堅決地相信你,相信美殉宛若從月光瀑布的一躍而下,順著彩虹而下的完美,之死,是值得的真實。我說,此時我並不能和年少摯友共同的承諾一樣堅貞跟隨你,「決不活過公元2000年!」,那虛無主義時代的你的信徒高高貼在牆上的標語,就像你在柏格曼的第七封印身著黑衣的行走,你,跟隨我也有好一陣子了吧,也想像電影一樣對我說:「是時候了啊!」是吧。我說,但此時我並不確定我想跟你走了,雖然可怕的咳嗽已經在我抵達教授研究室就已開始如瘟疫蔓延開來了,如萬丈波濤排山倒海向我的五臟六俯襲來,特別是肝臟,你知道的我身體最弱的地方。我想起了父親、童年歡樂的家庭、詩與師父們、自己年輕時追尋過的愛與誓言,那些餘溫猶存的記憶如照片,泛黃。此時的我依然似年輕時無所眷念,我說,但並不確定我想跟你走,只想透過你對於我的折磨觀察我/你。
【第三日】
整個月我喪失了對於身體慣有的自信,我喪失了助人的能力,這是唯一讓我覺得沮喪的事吧。練功場所仍然有許多期盼的眼神等待下手,與心靈的開導。你時常在我的左側冷眼旁觀我知道。那不算什麼,師父會這樣說我知道。我想起月前和師父去高雄看一個重症男士,曾經商場叱吒風雲的他已瘦如材骨,求生意志薄弱中帶著家庭的重荷嘮叨。,三十七、八歲得了末期的癌症,原是商場上叱吒風雲的青年企業家,瘦骨如材眼睛凹陷至深處,一股不能磨滅的英雄氣短的悲傷流傳在空氣中,兩個稚子與愛他的妻子。讓我回憶起這麼多年來嘗試從你的手中挽救許多人的歲月是否是樁騙局?自我欺騙的騙局?是不是當你的大手一揮,眼瞼一眨眼,其實我們所有人都必須跟你走?我不禁深深猶豫起來了,所謂的「隨緣助人」。於是你就看看錶,說我的時間也將至。整個六月我陷入可怕的痛楚,我也將自己隔絕於眾人之外,上課、說話、吃飯、做研究的我都不是我。你站在一旁面無表情地看著手錶,我說,你怎麼確定他就要跟你走,遺留一對稚子與未完成的夢想,尚未而立的年輕生命。你看著我們在卦中祈求奇蹟的傳遞,源源不絕的氣息傳入他虛弱的身體,他重重的咳嗽穿越時空撼動著我對自己的信仰,雖然可怕的症候已經在我抵達教授研究室就已開始如瘟疫蔓延開來了。你冷朝熱諷著我自以為是的幫人理療加氣的歲月,「沒有人曾因你的慈心而受惠」,你說,「他們終將皆死去,隨我而去!」你企圖有系統地打擊著我熱情入世的心,企圖讓愛口吐白沫在炎炎夏日中自取滅亡。我確實氣餒,但虛弱中不曾放棄。身邊的珍藏事物不吝給予,給予需要的人吧,我說,我曾經是你不二的信徒,換來的是贏弱的身軀與流浪的心靈,在多變的城市風候中兀自哆嗦。我遭受各式各樣的痛擊,來自黑暗界,但不曾心慌;因為死而復生的勇氣導引,「尚有許多期待救助的人啊!」,隔著厚重的隔音玻璃我聽見我自己的聲音雨中呼喊著暗啞無人理睬。
【第四日】
理性所構築的世界正面臨黑暗界力量輕蔑容易的摧毀。「凡存在即合理」是這個時代的標語。心靈隱藏最深的壓抑慾望肆無忌憚地在今日地球行走,其姿態宛若億萬年前獨霸這個星球的恐龍,經由價值中立的媒體、符號、政客與學術。我是一匹披著西裝外衣的狼。你經由一個被學校判定為精神病的陌生學生口中說出。她在暴雨的午後坐在H教室二樓的欄杆旁,身後的雨瘋狂淋濕了半身,她的眼神堅決攔住我:
「以上帝之名我認得你,你這校園裡最著名的老師,不要說不認識我,我千百年來反覆和你認識,你,你,你這熱血濟世的人,為什麼到此時還在堅持?看,看看我左臂上的刺青,921,我的傑作,我知道你此時是上帝,人們將信仰你,但你是匹披著西裝外衣的狼。不要排斥後代,不要排斥我,要讓你的後代目睹我還有不斷的傑作:地震、火災、山崩、洪峰、戰爭、狂瀉的股票、與愛恨離別。不要說不認識我,我千百年來反覆和你認識,就在廁所,人們覺得最為污穢的地方我們換帖結交,蟲蛆爬過我們欣喜的心情,頌揚黑暗之光吧,你這深受學生愛戴的,校園裡最著名的老師,你這匹披著西裝外衣的狼。以上帝之名我認得你。」
瘋狂倒影著文明這我們共同擁有的湖泊,我的心微微晃蕩,但是舟船不曾翻覆。她/你游離的眼神中我看得出你們對於我的篤定深感恐懼。我說。因為,你已察覺對抗你最為根本的武器已在我心萌芽。「相對於整個校園裡披著西裝外衣的狼,你的非理性是真正的理性。」我藉故從一偽善、輕挑、甜點形式的學院官僚會議中逃出時,對著雨後教室二樓的欄杆她/你坐過的地方,說了這樣的話。感謝你。虛無主義時代的我之後第一次感謝你。
【第五日】
你在世界蔓延的速度比我想像中快。我說。雷雨答伐研究室我批改學生期末報告的清靜間隙時我發現,自己無法回答〈藝術社會學〉課程中,一極為優秀的學生以下的詰問:「
首先,必要的是存在感的重新確立。近乎儀式性的招喚。
招喚那樣一種在生活的恬謐安逸中漸漸褪乏的曾反覆糾纏以倉皇悲切著的姿態的自我認證。
『怎麼樣才能證明我與眾不同? 』湖面上,楊牧以此詰問。
然而,在認定了必然的與眾不同之後呢?我們還可以拿什麼來面對存在?我們怎樣可以在虛妄的時間之中把握這當下不斷絮叨著的唯一主體?究竟,究竟人如何可以活著,而不僅僅只為了活著本身?
老師,我曾不斷不斷地想這麼問你,尤其在每一個你談到死亡的瞬間。
今年二月,我遭逢人生頭一次劇烈的背叛。關於情感,也關於我所仰賴的生存基石–相信。此時此刻我必須急切逆流回溯,回溯那曾教我瞬間崩解,如今卻僅僅如同皮膚上淡淡沉澱的暗紅印漬的疼痛。是傷痕嗎? 我甚至無法確定,然而,在那其中卻孕育了我頭一次完整自覺的蛻變。
並非一覺醒來發覺自己長成了一隻巨大的毒蟲,而是一點一滴詭異而瑰麗地,意識地看著骨皮肉的四肢逐漸幻化為繁多綿密帶著絨毛的細腳,背上拱起堅硬無比的厚殼卻也相對地擁有極其脆弱的柔軟胸腹,並沿著自己走過的痕跡沾染上黏膩稠濃的透明汁液。據說,這便是最明確的存在感。
正是為了存在本身的饑渴,亦同於對死亡的熱望。不是雪菲爾悲歌般殷切於對美的呼喚,然而那陰冷絕美的環墟的背對著自己的自己的影子,卻同樣迎面朝我踱步而來,在錯身的一剎那穿透置換,暗渡了腐敗,也暗渡無所謂傷害。於是人們以為我變得強壯,靈魂彷若愈加堅實。
只有我自己知道,文字如何同時拯救亦摧毀我,眼淚又是如何滴落在紙上卻化為矯飾的字詞,化為意識翻覆間我再也再也分不清的真實。
是嗎?再也沒有愛的能力了?但卻不為了傷害,而為了執迷於自己的存在姿態。為了這唯一的、絕對的、訴諸以靈魂為名義的、凝斂壓縮所有形容詞的卻早已亡滅的存在?
如果狂悲狂喜早在意識的辯證中得以層層剝落其灼熱的覆面,那麼楊牧的擔憂終將成為多餘。在創作的抽離中根本不存在有真正的狂悲狂喜,更遑論以此搭構藝術的殿堂。但如果,如果存在之神賜予以最後一次的真誠悲哀,我將致悼念於這些不復在的、關涉於活著的燃燒溫度。
在顧著舔舐傷口的時日中,我嚮往陳屍於雪山的淒美,渴求沉落寧靜的湖水,攜著雪菲爾一般明媚的面容,在皎潔月光下映出死亡的白肌。永恆,烙印在背叛者晦暗的瞳仁中。曾幾何時,背叛者的眼睛被鏡中的雙眸取代;我深切凝望著自己,只緣於那崇高無比的意識之遠離。在翻越之後我果真確立了自己的存在高度,帶著不可一世的自傲和睥睨的神情,明白終將沒有什麼可以重覆對我執行傷害。這具真真堅實的靈魂,『我答應賦它以永恆擴充,超越的潛能。凡經我心神鍛練者皆如是。』
除了,除了被拋擲的茫然和焦慮;我試著揣摩那道弧度。
除了,除了終於將赤裸裸地貼近於自身作為唯一的目的;竟無關於道德,只關乎美感。
是嗎?除了自己之外再也沒有愛的能力了?
或者,說愛太浮泛,然而我卻預視著自己即將成為『孤獨的孤獨的人』。
於是復原了之後我卻比以往更加疼痛難擔。如果致命的傷口不過是一道無謂的笑話。
或者在完全對稱的另一個半面上,我僅僅奢望擁有飛行當下的官能快悅,在穿破雲端的那一瞬間決然地背棄語言,再以極其委靡的醜態墮落,在急速下墜之中輕蔑於時間之神的任何眷顧。空氣承載不了我沉重的軀體和靈魂,整個整個地撞擊上堅硬的土地,霎時迸裂四散,碎末漫天覆地。
『若是如此純潔可以死去』,『在我還保有完整的真情和不著邊際的愛的時候』。
時而決定毫不猶豫地腐爛,化為天地的一部分;但時而卻又認真地感到羞恥起來。作為一個絕對者,怎麼能夠恣意放縱著自己最最直接純粹的欲望?!
便永恆地晃盪在兩個極端之間。日益擴大的裂痕,只要一不留意便將陷落,動彈不得;連渴求死亡都是多餘的幸福。
軟弱和堅硬的交相辯證、疼痛的收服以釀造更為巨大的、意識抽離之後無能於愛的感傷對比著近貼官能的狂悲狂喜……,或者,一切只不過又是舔舐了另一種同樣單薄的傷口,並且採取了如此悲情的形式來成全我再一次的文字療癒接連著暗地裡焦躁的自我認證。
但老師,那股注定自我摧毀的痛楚,你能明白的。」
【第六日】
「還能有所摧毀的時代才有幸福。」今日我突然想起年少時光所寫下的這句子,你一定記得的,二十三歲的我,拿隻土產的甘蔗凌晨兩點和虛無同黨騎著野狼摩托車狂奔台北城的時代你的容顏是無法抹除的完美問我歸鄉何在那時的痛苦只有能以勝過死亡的瘋癲和你分享。我說「沒事了,真的沒事了,謝謝你載我一程。」俟你離開後,我面對一盞孤燈與夫一坪大的斗室拿起美工刀就往手上的血管劃去而復返的你撞開木門立刻奪掉我的刀說怎麼這麼傻這一切是為什麼?你看看我小小的床頭,凌亂的紙筆上面書寫的一改再改的詩稿隱約標題為給奧菲莉亞的十四行詩之類,你看看我過得是怎樣的日子,每日必須翻越公館旁的小山頭到森林系館去與不愛我的奧菲莉亞編織一道只有自己相信的愛煞世人的高牆你說我如何苟活於世?在系館的留言簿我的心血結晶句子串成的詩篇卻必須兀自忍受著業餘與競逐者的嘲笑與冷漠我如何能保全對詩之愛?「沒事了,真的沒事了。」現在,我聽到這樣的謊言像瘟疫一樣的蔓延在這冠冕堂皇的國度,無所摧毀的時代有著精神分裂的幸福。
【第七日】
這將是不能完成的一日,我鄭重告訴你,以浮士德之名,因為你尚未以梅菲斯特之姿出現,讓我對著世界說「我滿意了,請帶我走吧!」我將以最為頑強的意志與你對峙如查拉杜斯屈拉,以最柔軟的聲調和你共處如老子之水,以這沒有日期年月日的不能完成的一日之樹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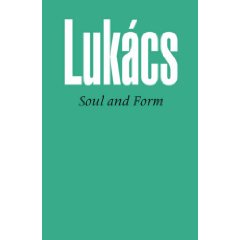
 盧卡奇
盧卡奇 